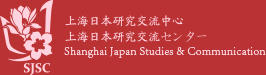来源:环球时报
日本年轻人对政治的态度正成为舆论关注焦点。7月的参议院选举,年轻人投票取向的变化,成为自民党惨败、参政党等激进民粹政党兴起的一大原因。另一方面,“后石破”首相人选,能力存疑、但“年轻”“有活力”的小泉进次郎、小林鹰之等成为热门,而那些经验丰富的资深政治家在“最适任首相”民调中远远落后于小泉等人。在日本这个高度老龄化的社会,到底发生了什么,让“年轻人”如此受到关注?
欧美民主政治中已广为人知的“脱嵌”或者“非代表性危机”,在日本表现得越来越突出。过去,社会群体通过政党来表达诉求,各大政党一般都有比较明确、稳固的社会支持基础。具体到自民党,冷战时期该党拥有众多业界团体的支持,其拥趸很多都是“有组织的人”。“组织票”成为选举中的“铁票”,是支撑自民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因素。但现在自民党的组织票大幅缩水,意味着相当多的选民不再愿意加入某一社会群体,成为“游离者”。20世纪60年代不支持特定政党的“无党派层”选民只有6%,而《朝日新闻》2024年的一份民调显示,“无党派层”达到59%。也就是说,原本自民党的民众根基已经“流体化”。“无党派层”的流向,往往会造成日本选举结果难以预料的变化。
在无党派阶层中,年轻人占据相当大的比重,因为年龄越小,“非组织化”越明显。据日本一般社团法人PMI的调查,20—30岁的日本人,有57.5%没有特定支持政党。这些人容易受到社会焦点议题与氛围的影响,出现向某一方集中投票的情况。在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,参政党和国民民主党的大幅跃进,就是这种集中投票的结果。
“现代民主制度的缺陷——短视近利漠视未来”,英国广播公司之前的一个标题为观察当前的日本政治提供了注脚。相比于那些宏大的问题,日本年轻人更关心涉及自身利益的议题,比如学费、就业、收入增长等。20—30岁的年轻人中,有1/3是非正式工,不仅工资低,工作还不稳定,缺乏归属感。能够进入大企业端“长期饭碗”的毕竟是少数,那些中小企业的正式工,收入实际上也并不稳定。
经济基础不稳定的日本年轻人希望改变现状,对民粹主张最为敏感,于是就有了那些投其所好的政党:你们希望增加收入,可以,我们主张减税;你们觉得外国人抢了你们机会,可以,我们提出反移民政策。参政党和国民民主党就是这样的政党。根据《日本经济新闻》参议院选前民调,18—29岁年轻人中,愿意投给国民民主党的达到29%,投给参政党的有20%,明显高于投给自民党的比率。而在安倍晋三内阁和菅义伟内阁时期,18—29岁年轻人对自民党的支持率曾长期维持在50%—60%的高位。原因无他,当时自民党的“安倍经济学”,本质上也属民粹政策。
选民的流量化带来自民党年轻政治明星的崛起。在论资排辈的自民党,政治资历按当选议员次数来定。曾几何时,自民党只有各派阀领袖才有资格竞选党总裁,也只有当过党干事长、大藏相(财务相)、外相等重要职位的重量级政治家才有竞选总裁的底气。然而,观察这次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热门人选,小泉进次郎是1981年生的小字辈,1974年的小林鹰之虽然不算太年轻,但他2012年才首次当选议员,资历很浅。高市早苗和林芳正都是1961年生人,虽然已经60岁出头,但在自民党内也只能算“中等年资”。
之所以“年轻人”在自民党内出头,是因为党总裁选举不再是以能力为标准,而是以“能否在选举中帮助自民党获胜”为准绳,能从选民手中挖到选票的总裁就是好总裁。可以说,过去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是“硬实力”的比拼,而现在则是所谓“形象”的比拼。
自民党总裁选举之所以会比拼“形象”,和上述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的变化息息相关。冷战时期,日本民众更倾向于根据政策来决定投票取向,进入新世纪后,随着日本政治的媒体化,政治家的形象在投票行为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,不管有没有能力,形象好,就很可能拉来选票。若是有一些能够抓住选民痒点的民粹主张,那就更好了。
在日本,选民的浅层化和政治家的浅层化,已经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。浅层的选民形成流量的主体,而政界为了获取这些流量,纷纷推出能够吸引这些流量的民粹政策或者政治明星。网络化时代对日本政治的影响,值得继续观察。(作者霍建岗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)